✣ 启示录18:4 离开那城的呼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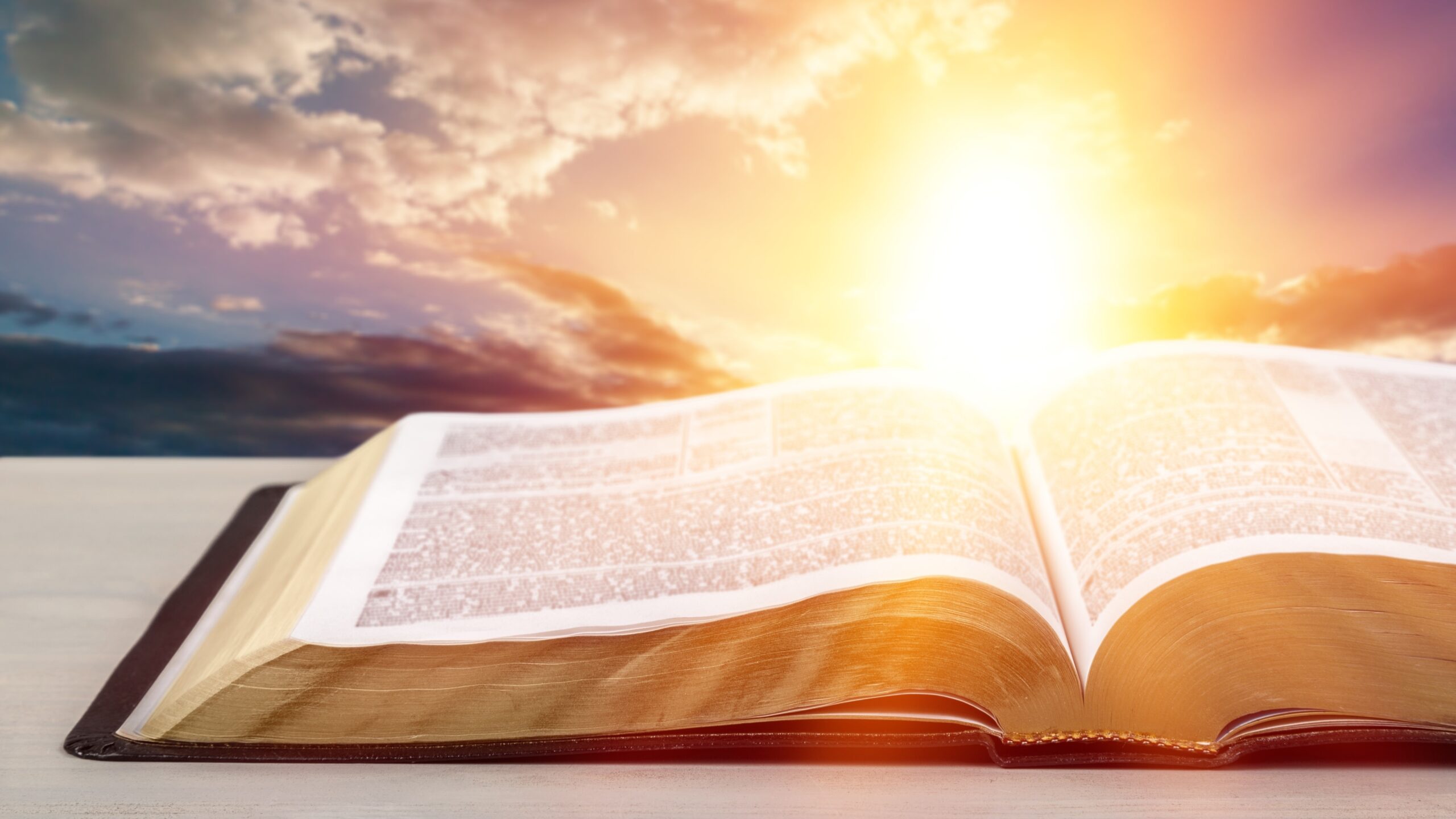
七个异象的结尾是末后的七灾(15:1),这七灾是七位天使将盛满了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(15:5-16:21)。七碗与七号(8:6-11:19)的异象有许多相似之处,都是通过埃及十灾的景象,象征神对迫害信徒和敬拜偶像的不悔改之人的审判(9:20-21; 16:2-9),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达到完全(11:15-19; 16:12-21)。这一切审判既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公义,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(11:13,15-16; 15:4,8; 16:9; 19:1-7)。七碗与七号的异象也有不同之处,主要体现在受害的对象和受灾的程度,但这不意味着它们有时间上的先后,而更可能是在描述同一阶段的事件(Beale, G. K.),即七信、七印、七号、七异象所启示的从主复活升天到主再次降临期间所发生的事。七碗的异象是对七号的补充和强化,正如七异象是对七印的补充和深化。在七碗的审判中,前五碗是主再来之前,对地上迫害信徒和敬拜偶像之人的审判(16:2-11);第六和第七碗是主再来之时,对整个邪恶世界和邪灵的终极审判(16:12-21);17:1-20:15则是对终极审判的详细阐述。在12:1-15:4的七异象中,相继兴起了龙(12:1-18)、兽和假先知(13:1-18) [注:龙代表撒但,第二只兽代表假先知]、以及败坏列国的巴比伦(14:8)。在16:12-20:15的审判中,对龙、兽和假先知、巴比伦的审判,以与前面相反的顺序呈现:首先是巴比伦的倾覆(16:17-19:8),然后是兽和假先知的毁灭(19:17-20),最后是撒但的灭亡(20:10),同时也伴随着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经历第二次的死(20:11-15)。审判的顺序未必代表着时间顺序,更可能是在末后同时发生。17:1-19:8详细启示了巴比伦将要遭受的审判:首先是描述巴比伦的淫乱(17:1-18),然后是阐述巴比伦的毁灭及其意义(18:1-19:8),中间穿插了神对信徒的呼吁:”从那城出来吧,我的子民!免得在她的罪上有分,受她所受的灾难。”(18:4)
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借用了历史上的巴比伦 (耶51:12-13),既代表着悖逆的以色列(结16:38)和教会里面的背道者(2:20-22),也代表着以罗马为首的外邦邪恶政权(17:4-6)。巴比伦被比喻为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,地上的众王都跟她行过淫,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她淫乱的酒醉了(17:1)。”淫妇”的比喻表明巴比伦引诱人远离神,”坐在众水之上”表明巴比伦有统治列国的权柄(17:18; 18:7),”淫乱的酒”表明巴比伦通过宗教和经济上的强大影响力(18:3,9-19,23; 13:16-17; 赛23:17; 何4:11-12),迷惑列国与巴比伦联合(18:23)。巴比伦不只是拥有强权和荣华(17:1,4),更是在宗教上与兽联合(17:3),这兽就是迷惑和逼迫圣徒的撒但之党羽(13:1-17);因此,巴比伦被称为”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”(17:5),并且杀害为耶稣作见证的圣徒(17:6; 18:24)。当约翰因为看见骑着兽的妇人而惊奇时,天使向他启示了关于兽和妇人的奥秘。兽的奥秘在于,它虽然有代表权柄的七头十角(17:3),如同羊羔拥有代表权柄的七角七眼(5:6),但是它同羊羔的争战必定会失败,因为羊羔才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(17:14)。兽被描述为”先前在、现今不在,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,然后走向灭亡”(17:8),这与兽受过致命伤又医好(13:3)、撒但被捆绑后又暂时被释放(20:2-3),表达了同样的意思:兽和撒但已经被击败,但是它们还有短暂的活跃时间,但最终会被彻底毁灭(19:19-20; 20:10)。兽所经历的三个阶段——先前在、现今不在、将来要出现并且走向灭亡,正是在”盗版”受难之后又复活的基督所经历的三个阶段——”我是首先的,我是末后的,又是永活的;我曾经死过,看哪,现在又活着,直活到永永远远”(1:18; 2:8);兽的最终命运是灭亡,基督却要掌权到永远(11:17; 19:6)。妇人的奥秘在于,虽然她的装饰十分华美(17:4),如同羊羔婚筵上的装饰(21:18-21),然而她并不是基督的新妇,而是引诱人行淫乱的耶洗别(2:20-24);她的结局不单是要受到神的审判(18:1-3),在审判之前也要照着神的旨意,被地上的众王和兽憎恨和攻击(17:15-17)。
17:1-18启示了巴比伦的淫行,18:1-19:6则详细启示了巴比伦的毁灭及其意义。18:1-19:8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:宣告巴比伦的毁灭,并且呼吁圣徒逃离巴比伦(18:1-8);与巴比伦联合的地上众王、商人和海上的水手为巴比伦的毁灭而哀哭,因为巴比伦的命运也代表着他们的命运 (18:9-19);圣徒却为巴比伦的毁灭而欢喜,因为神为圣徒伸了流血的冤(18:20-24);巴比伦的毁灭表明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,使神的荣耀得着颂赞(19:1-8)。
启示录藉着多重异象预告了末世要显现的灾难和审判,同时也呼吁信徒在这些灾难中警醒、忍耐和自洁:神在七信中呼吁在患难中的教会忠心至死(2:10),在七印的灾难中呼吁被杀的信徒继续等候(6:11),在七异象中呼吁信徒要有忍耐、信心、智慧和悟性(13:10,18; 14:12),在七碗的审判中呼吁信徒要警醒、看守自己的衣服(16:15),在巴比伦的审判中呼吁信徒要有智慧的心(17:9)、从巴比伦城出来(18:4)。巴比伦城代表着与天上永恒之城相对的地上的一切淫乱(17:1-5)、强权(17:18)、骄傲(18:7)、奢华(18:9)、享乐(18:14)、财富(18:19)、进步(18:22)、诱惑(18:23),等等;巴比伦城吸引人沉醉在其中,与之一同灭亡。因此,信徒在末世不仅要忍受严重的逼迫,还要抵抗强大的诱惑,能够分辨”三一魔”(16:13; 20:10)与三一神、淫妇(17:4)与新妇(21:2)、巴比伦大城与耶路撒冷圣城(21:2)。当巴比伦用淫乱的酒使地上的人都喝醉了的时候(17:2; 18:3),信徒必须保持清醒,要从巴比伦城出来(18:4),敬拜那真实、公义、荣耀的神(19:1-2)!
C.S. 路易斯在他的著作《纳尼亚传奇:银椅》中,用童话故事的方式,深刻展示了魔鬼所创造的虚假世界的力量和诱惑是多么强大。在《银椅》的故事中, 凯斯宾国王的儿子瑞廉王子被蛇精诱走,尤斯塔斯和吉尔被阿斯兰召唤到纳尼亚解救王子[注:在纳尼亚的故事中,阿斯兰是一只狮子,代表着基督教的神]。阿斯兰给了他们四条指示,前三条他们都违背了,并且因此吃了很多苦;最后他们同沼泽怪普德格伦一起,根据指示来到地下王国 ,碰到了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骑士。骑士告诉他们,自己深受魔法的折磨和约束,只有夫人能使他解脱;但每晚有一个小时,魔法会生效并使他疯癫,一小时过后他才会清醒过来;到时候必须将他绑起来,否则他就会变成类似毒蛇的东西杀掉身边的人。那天碰巧夫人不在,魔法即将发作之时,尤斯塔斯一行人想要在一旁观摩;骑士警告他们,在他发作的时候不管他如何威逼利诱,都不可听他的任何话!等到魔法发作的时候,骑士被死死地捆绑着,无论是请求还是恐吓都无济于事;之后他强作镇定说,我其实只有在这一小时里才是清醒的,其余时间都在魔法的诱惑下,而夫人就是魔鬼!但他们仍然不为所动。骑士穷尽一切办法都得不到帮助,最后他说,”我要求你们把我放了,爽快点!以全部的恐惧和全部的爱的名义, 以上面世界明亮的天的名义,以伟大的狮王,以阿斯兰本人的名义,我命令你们!” 他们吃惊地大叫起来,这正是阿斯兰的第四条指示,不能再错过了! 他们解开了绳子,骑士斩碎带有魔法的银椅,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—瑞廉王子。骑士的夫人回来看到这一切,就对他们施了魔法;他们逐渐变得迷迷糊糊,地上的世界,天空的太阳,美丽的狮王,变得越来越模糊,似乎只是想象、只是童话、只是梦,只有眼前的地下世界才是真实的… 沼泽怪仍在坚持同魔法抗争,他索性将脚伸进火盆,灼痛和烧焦味儿让大家开始清醒;在众人的帮助下,王子杀掉了蛇精。
《银椅》中由蛇精所掌控的地下世界,正映射着现实世界中由魔鬼所掌控的”巴比伦城”。在城中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、却不知道是沉醉的,以为是自由的、却不知道是被束缚的,以为眼见的世界是真实和唯一的、却不知道是虚空和即将被毁灭的。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和拯救,我们也会同世人一样在沉醉中灭亡。然而,我们虽然得了神的指示,知道要”从那城出来”,却常常会违背神的命令,继续爱这个世界(约一1:15),停留在城里享受暂时的罪中之乐。如今的巴比伦城不是一个地点,而是一种力量,一种吸引人远离神的邪恶力量。”从那城出来”不是指人的身体离开某个地方,而是指人的心抵挡魔鬼、与神亲近(雅4:7-8)。在当今的世代,撒但所使用的一个强大武器就是网络。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,每天都要通过网络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大量的信息;许多人除了睡觉和工作之外,几乎都沉浸在网络世界中,完全没有安静默想的时间。对基督徒来说,网络所带来的属灵危害是显而易见的:因着上网的便利,许多信徒常常会以了解咨询或休闲放松为由,投入过多的时间在网络上,远远超过了读经、祷告、灵修和服事的时间,以致于内心被人造的虚拟乐园、败坏的世俗价值观、各式各样虚假甚至污秽的信息所填充和捆绑——包括新闻、影视、综艺、短视频、社交媒体、游戏、色情、暴力等等,从而对属灵的事失去兴趣。魔鬼曾经借助宗教、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力量构建了迷惑列国的大巴比伦城(14:8),如今却借助网络构建了牢笼人心的无形的巴比伦城,让无数非信徒和信徒都沉醉其中!愿我们都能够有智慧的心(17:9),不可忽视巴比伦城的悲惨结局(18:2),不要忘记神对圣徒”从那城出来”的呼吁(18:4),要逃离那淫乱和灭亡之城,竭力地追求那些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事(腓4:8),直等到荣耀的神降临、带来真实和公义的审判(19:1-2)。
文 / 周元圣
